当罗永浩与周鸿祎的 AI 对谈再次占据社交版面,当李想的落泪片段在短视频平台反复刷屏,2025 年的中文互联网似乎确信:视频播客终于迎来了 “破圈时刻”。但在这场由名人与大厂共同制造的热闹背后,《置顶废话》主播肉松的疑问更显真实:“谁会愿意花时间单纯看两个普通人聊天?” 这道追问,揭开了视频播客繁荣表象下的深层裂痕 —— 它既未成为音频播客的进化方向,也未构建出可持续的内容生态,更像是一场名人借势、平台试水的短暂狂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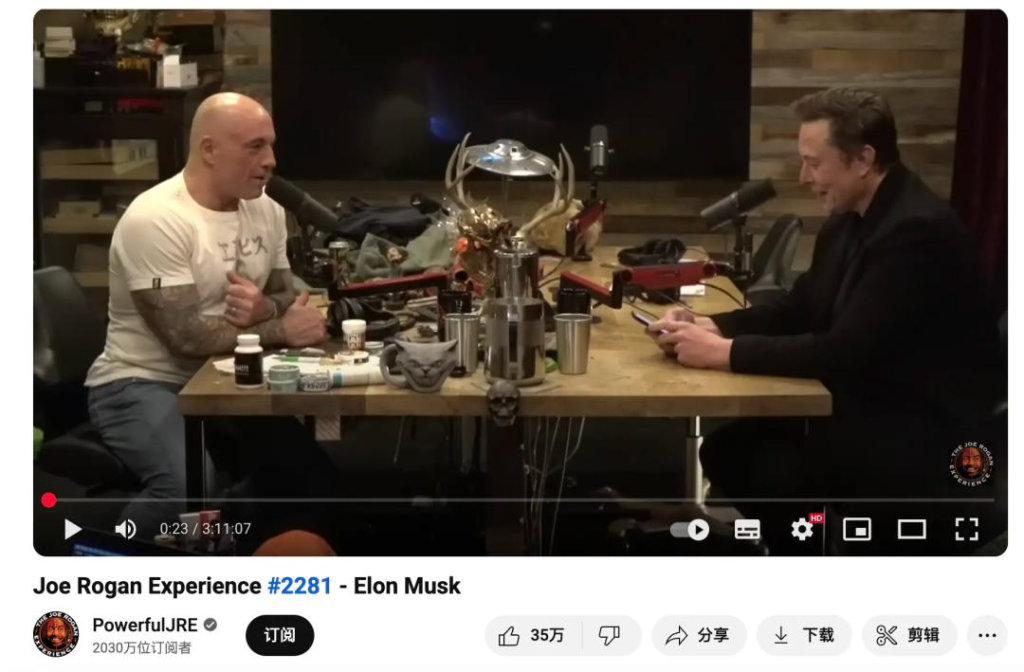
热潮真相:名人包装下的 “伪播客” 狂欢
视频播客的当前热度,本质是名人效应与内容焦虑碰撞的产物。罗永浩、鲁豫等名嘴的入场,与其说是深耕播客赛道,不如说是借用 “播客” 标签重构访谈节目形态。李想落泪、窦文涛被 “收养” 等病毒式传播的片段,精准击中了大众的娱乐化需求,却与播客核心的 “深度陪伴” 属性背道而驰。这些动辄百万播放的节目,实则是披着播客外衣的综艺化内容,依靠嘉宾咖位而非内容价值吸引流量。
美国 “播客之王” Joe Rogan 的成功,常被视作中文视频播客的对标范本。但二者存在本质差异:Joe Rogan 的节目以观点碰撞和深度对话构建核心吸引力,访谈对象的顶流身份是附加值而非全部;而国内名人视频播客中,嘉宾的个人话题早已盖过对话本身,周鸿祎的 AI 见解远不如其过往言论的 “切片” 传播度高。这种 “话题优先于内容” 的倾向,使得视频播客沦为碎片化情绪的集散地,而非信息增量的供给源。
大厂的流量加码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虚假繁荣。B 站投入 10 亿级流量、提供免费录制场地,小红书推出专属话题与曝光资源,抖音开辟精选入口,本质都是将视频播客作为内容生态的 “补充拼图”。B 站对明星大咖节目的侧重,实则是用低成本撬动高价值流量;小红书 15-20 分钟的内容时长,与用户碎片化浏览习惯形成天然矛盾;抖音的谨慎试水,更凸显出平台对其商业化效率的疑虑。这场平台主导的热度,从未真正服务于播客生态的成长。
生态分裂:创作者的选择困境与生存现实
“做还是不做视频播客?” 这个问题正在将中文播客群体撕裂成两大阵营,而背后是创作逻辑与生存成本的深层冲突。对头部主播刘飞而言,视频播客是 “生造的概念”—— 名人做的是访谈综艺,知识博主的内容无需依赖画面,本质都是给传统内容套上新壳,并未形成独特形态。这种认知让他对视频化持观望态度,毕竟 80 万订阅用户的核心需求仍是 “闭屏收听” 的陪伴感。
中小播客主的犹豫则更现实。肉松和室友运营的《置顶废话》刚突破 1200 订阅,她们的顾虑直白却致命:“普通人的聊天没有观赏价值”。视频化意味着制作成本的指数级攀升,从机位、打光到剪辑,单枪匹马的创作者难以匹敌专业视频团队;而若只是简单架起镜头,慢节奏、低画面信息量的内容在中长视频赛道毫无竞争力。这种 “不升级等死、升级找死” 的困境,成为多数中小播客主的共同难题。
乐观派的声音同样存在,但更多源于对音频媒介局限性的焦虑。从业 5 年的广播人直言声音媒介 “天然弱势”,视频化是破局必经之路;狂喜播客节创始人关雅荻强调 “有话要说比技术重要”,鼓励新人抓住曝光机会;播客公社创始人老袁则认为,只要支持闭屏收听就具备播客属性,视频化能打破 “精英化刻板印象”。但这些观点难以解决核心矛盾:当制作门槛与用户需求脱节,理想中的 “人人可做” 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。
更残酷的是生存现实的分化。头部名人靠着自带流量轻松斩获广告与曝光,订阅数近 50 万的节目单条口播广告报价可达 3.8 万元;而中腰部创作者却难以触达商业化资源,多数仍在 “为爱发电”。有播客主透露,一年仅有一两次接广告的机会,甚至为维持调性拒绝外卖券等广告。视频化带来的成本压力,只会让这种马太效应愈发显著 —— 能负担专业制作的头部强者恒强,中小创作者则被彻底挡在门外。
商业化死结:流量、数据与场景的三重桎梏
视频播客的热闹未能解开中文播客的老难题:商业化始终停留在 “纸面可行” 的阶段。2024 年中文播客广告总收入仅 33 亿元,远低于短视频平台;能靠订阅收入生存的节目占比不足 5%,这个数字在视频化浪潮中并未得到实质改善。广告与订阅两大变现路径的堵塞,源于流量、数据与场景的三重桎梏。
广告市场的 “买方主导” 格局从未改变。定期投放的品牌集中在消费电子、生活服务等细分领域,整体需求有限;更关键的是效果追踪难题 —— 音频时代的口播广告无法量化收听率与转化率,视频化虽能展示画面,但用户是否关注广告内容仍难以监测。广告主对 ROI 的追求,与播客 “软性宣传” 的属性天然冲突,多数投放只是品牌部门的 “工作亮点” 或剩余预算消耗,难以形成稳定需求。
用户规模与付费意愿的失衡同样致命。尽管 2025 年中文播客听众预计突破 1.5 亿,且以高学历、高黏性的 “三高人群” 为主,但相较于抖音、B 站等平台仍显小众。更核心的是付费习惯尚未养成:单集 4-10 元、专题 30-300 元的定价,对习惯免费内容的用户而言门槛过高;而播客主提供的 “深度内容”,又难以转化为明确的付费价值感知。视频化带来的用户增量,多是追求娱乐话题的泛众,而非愿意为深度内容付费的核心听众。
场景错位则让视频化的商业化想象落空。播客的核心优势是适配 “眼睛被占据” 的通勤、健身等场景,而视频化强行将其拉入 “视觉优先” 的消费场景,直面影视剧、短视频、综艺的竞争。当用户有时间看视频时,更倾向选择信息密度更高、视听更刺激的内容,视频播客往往成为末位选项。这种场景与需求的错配,使得视频化非但未能拓宽商业边界,反而稀释了播客的核心竞争力。
未来迷思:风口过后,播客何去何从
关于视频播客的未来,乐观与悲观的预判形成鲜明对立,但都指向同一个结论:这不是能速成的风口,而是需要长期培育的生态。刘飞的悲观源于对市场基础的判断 —— 美国有长距离通勤的 “听播客” 土壤,国内缺乏类似需求,《圆桌派》等优质对谈节目始终小众,视频化难以改变用户习惯。在他看来,当前的热度只能让更多人知道播客,却培育不出足够的深度内容消费者。
老袁的乐观则建立在生态成熟的漫长等待上。他认为美国市场的成功源于 “认知统一性”:播客像社交媒体一样人人可做,无关形式与名气。视频化若能打破认知混乱,让播客回归 “自我表达工具” 的本质,随着创作者与用户基数的积累,商业化自然水到渠成。但他也坦言,这个过程中多数创作者只能将播客作为 “表达出口”,而非谋生工具,“没有大爆款,也难有实际回报”。
对普通创作者而言,当下的最优解或许是 “回归本质”。与其追逐视频化的热潮,不如深耕音频内容的核心价值 —— 在通勤、睡前等场景中提供不可替代的陪伴与信息增量。小宇宙等音频平台 “只涨不跌” 的流量增长,证明了核心需求的稳定性。而平台真正该做的,不是用流量催生虚假繁荣,而是搭建更完善的商业化基础设施:建立广告定价体系、优化付费订阅体验、完善数据监测机制,让创作者能靠内容本身获得回报。
当罗永浩们的话题热度褪去,当大厂的流量扶持转向下一个风口,视频播客的泡沫终将破裂。但那些真正沉淀下来的声音 —— 无论是在耳机里还是屏幕上 —— 那些能提供思考、陪伴与共鸣的内容,终将穿越周期。中文播客的未来,从来不在名人的眼泪里,也不在平台的流量池里,而在每一个愿意 “为爱发电” 的创作者与愿意静心倾听的听众之间。这场漫长的等待,才刚刚开始。
发表回复